何与怀
一
试想像这么一个场面:在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南半球、远离中国的英联邦国度,在悉尼这个西方城市中的一间中式酒楼,几十位华裔诗人聚会,两位本地电台汉语主持人和一位悉尼大学汉语教师,以朝圣般的虔诚,共同朗诵一首诗,全场屏息倾听,结束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大家无不感动、钦佩,甚至肃然起敬……
这是澳州《酒井园》诗社2003年一个春日举行的活动,朗诵的诗是刘虹的《致乳房》。
二
2003年3月4日,我收到刘虹的电邮,告诉我她大约一周后动手术。她说:我患乳腺肿瘤多种,先取出一个最危险的(当时被广州和深圳几家医院疑为乳腺癌)。我主要是身边无人照顾,加上体质太差,心里有点害怕。还有报社正在合并动荡时期,不宜住院请假;正在筹划的诗歌活动也骑虎难下。最主要的,是女人对这种手术都有本能的拒绝心理。我的身体从小就多灾多难,常常要承受病痛煎熬。刘虹最后对我凄然地说,再给我一点勇气吧。谢谢!又说,可以谈谈审读我诗稿的意见吗,感觉也行,这真是我的精神寄托啊!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题为“刘虹致谢!”的电邮。信上说,我会记住你的鼓励,愿上苍保佑我——手术提前了,再联系。
此后,我一直预感刘虹有好消息给我。3月20号一早打开信箱,果然!刘虹告诉我,她已动了乳腺手术,万幸是良性的,上苍保佑!刚刚出院,今天提前上班了——工作环境压力大,不敢休完病假。
她随信附了一首诗,就是《致乳房》。
她问我,你们报纸能发么?
我说,这正是我最想发的杰作。
《致乳房》发在《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五十八期上(2003年4月12日)。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衆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
我自信我的见解不错。
后来,刘虹告诉我一连串的好消息:《致乳房》在《星星》2003年6月号发出后,立即被国家最高级别的《中华文学选刊》推举选用,以最快速度发在第八期扉页上了。接着,又被《诗刊》十一期选载了。陆续还有《诗歌月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亚省时报》、马来西亚《清流》杂志。此诗并在当年的全国诗赛中获奖。刘虹一再强调:“我永远记得是你慧眼识珠首发的,你是这首作品的真正伯乐!再次谢谢你!”
我对“伯乐”的赞谢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我希望所有读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对自己精神疆域的坚守。这首诗现在誉满海内外,但它是在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下写成的啊!
回到2003年3月8日那天。
刘虹那天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独自去医院办理住院及手术的繁冗手续,晚上回到形影相吊的家,备感孤凄恐慌无助,自哀自怜中又心有不甘。她拼命压住自己的软弱、绝望的念头,或者相反——绝望的念头正在打垮她:以为一生在绝望中挣扎,现在可能真的走到头了。一个单身女性孤独无助地承受也许是癌症大手术的身体重创已经够惨,何况又要痛失女性美的标志!何况痛失之后还要面对生死难定的生命挣扎!她想到即使侥幸不死于癌,但她纯情至性付出血泪代价、守望了大半生的爱情从此更加遥不可及!即使能苟延残喘,可生命的质量此后再也谈不上了。她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现实能力……
死到临头的感觉,又不甘心就此了断,此时她突然想到必须用一首诗,记录这种痛苦的生命高峰体验,也许这首诗就是她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留痕……
这是三八妇女节之夜。《致乳房》在泪中急就——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
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
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
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
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绝笔。它差不多是被当作遗嘱写的。所以,刘虹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凛冽、决绝而又澎湃,基本是一气呵成。又恰逢妇女节,全世界关注女性的时刻,但“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她却只能凄哀地泣血而歌,自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充满了生命的悖论!
《致乳房》全诗共五章,每章十一行,形式上比较整齐。以刘虹当时的心境和紧迫的时间,她根本来不及考虑诗歌形式的问题,可以说是自然流淌。现在人们都一致指出,这首诗的形式是其主旨的非常恰当、完美的载体。刘虹谦虚地说这属于“歪打正着”,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三
许多论者都赞同,《致乳房》可以视作深度诗写的成功范本(对比之下,当代中国诗坛泛滥一时的下半身诗歌作者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是这些诗人毫无羞愧之心),体现了刘虹坚定的理想主义诗写立场,她要传达出: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心地高洁、精神丰富、有灵魂持守的女性,在深刻的自我认定之上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当然,以刘虹的人生观和精神疆域,她不可能局限于一己的命运悲哀,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标于世俗之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对生命和世界的审视与浩歌。
再以《打工的名字》为例。这是刘虹另一首重要的作品,动笔于2003年元月,3月修改定稿。一年之后,刘虹告诉我,此诗近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几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包括《中国杂文选刊》,但她并不以为然——文学媒体也是跟风,跟中央“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文件精神之风。而这首诗远远早于此风之前写成,早先投稿却无人搭理。一家国家级大刊物在投稿8个月后、“风”盛之时,才又翻出来,说诗好,要发,责怪刘虹已转投边塞小刊《绿风》发出了(!)。
《打工的名字》第一节整个是“名称”的排列: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学名 进城务工者
别名 三无人员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真是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的排列。谁都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悖论和讽刺意味:农民工名实不相符、名字与名字演进的自相矛盾、和历史更迭中被欺骗的命运。
下面几节都是农民工命运的讨论的展开和深入。诗这样结尾: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
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
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
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
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後值是梁山泊还是
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刘虹说,之所以修改了好几遍才定稿,就是想让自己的热血走到笔端时冷凝一些,不是直接为打工者“热呼”,而是“冷嘲”社会的自欺欺人,唤起打工者对自己命运的真切认识和权益维护意识,并警示官府不要把人“逼上梁山”。
在书写形式上,《打工的名字》保持了刘虹一贯的风格:追求情绪的内在节奏感、语言内核的张力,以及词语质地的强烈对比与碰撞。正如一些诗评家所称赞的,这首诗的特点是写得比较“智性”。刘虹自己调侃说,她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大大强过她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如果被传统诗论判定,实为一个“不适合写诗”的人。但她始终看重诗里所传达的思想——这块土地上启蒙的使命远未完成。
刘虹的创作表明,她确实一贯重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诗写者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她之所以能在中央文件之前写出此诗(她此类关注底层群体的作品还有多篇),除了她一直“坚持要用一颗朴素的灵魂倾听大地痛苦的呻吟、绝不切断诗写者与现实存在的血脉相连”这样的写作观念之外,还因为她在新闻媒体工作多年,前几年还负责过新闻投诉热线,经常接触到底层打工者的不平之声、呼救之声,声声让人不安:这社会真是太黑了!简直有官逼民反的势头!刘虹在工作中尽力帮他们向上投诉以解危难,但这并不足以平静她的良心。正如她自己所说:
“若我不写出来,我的笔也会不安的。这个时代仍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的、有热血的诗人,社会的‘痛点’也是自己生命之痛!一个诗人的痛感神经麻木,就不配写诗了。所以我一直不能认同让诗歌回到内心、只抒一己小悲欢、小自恋的写作姿态。”
前不久,刘虹来信说她正在编辑新诗集,出版商催着交稿,但还是要等我的回音——她叫我看看哪一辑排第一、第二?看看那首诗排第一、第二位置?她说是“求教”,我可担当不起,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就按现在第一辑排第一,而且,第一首应该改为《打工的名字》,第二首为《一座山——致钟南山》……,这样更突出这部诗集与众不同——更注重其社会政治意义。
她在这部2004年底出版的新诗集《刘虹的诗》的自序中强调: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四
三十年来,刘虹写出一首首令人瞩目的诗章,也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她自己较喜欢的代表作是:《向大海》、《故乡》、《夜读郭路生》、《欢乐》、《探月》、《西部谣曲》、《一座山》、《致乳房》、《打工的名字》、《说白》、《我歌颂重和大》……阅读这些诗章,谁都会有所觉察:显然,刘虹选择了一种“用生命写诗”的诗写姿态。而她选择了这种诗写姿态,肯定就是选择了生活的冒险与苦难。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刘虹呢?
我第一次见到刘虹是在2002年12月,当时我从遥远的南半球来到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参加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开幕前一天下午空档,同是诗会代表的刘虹和香港的海恋来约我去拜访南京的《扬子江》诗刊社,该刊刚刚发表了刘虹的作品,她已经与子川主编约好。于是我见到一位年近中年的女子,身穿火红的大衣,整洁自爱;性格也很火红,热情爽朗,一见如故。
这就是刘虹。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书名是《结局与开始》。我说怎么是北岛的味道,她说她开始写诗并在诗坛小有名声的时候正是北岛的时代,《结局与开始》的确是仿用北岛一首诗的标题《结局或开始》,是概括她当时生活的“临界状态”——希望旧的结束,新的开始,虽然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上,至今都难以对这一状态有效突破,她说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期待吧。
与结局、开始相关,刘虹迄今经历了她生命中两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她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她五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诗的涂鸦、直至十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她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她诗的今生今世。她在大西北一住十年。
一九七六年她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时,跟朦胧诗一代人北岛、舒婷他们的创作主题比较接近,是对传统的叛逆。但她那时主要是批判的角度,而个人生存的痛切感远远不如后来在深圳那样深切。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优越的环境长大的她,那时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底层的东西。最早让她受震动、开始思考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还有上大学以后接触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思想解放比较早的老红卫兵,对她影响比较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为什么跟朦胧诗思想渊源比较近。
一九八七年春,刘虹经历一场情感重大打击以致罹患伤寒,报了病危。当年底,重症初愈、不待好好休养,却草草收拾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W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飞机独闯深圳,开始了她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这样,时代与社会就在刘虹身上制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空前释放了人的欲望,出现大面积的人心失守,道德沦丧;而她恰恰在深圳这个人性大实验场的地方坚持她那种精神高蹈的诗写,好像在跟商业社会唱反调。她说,这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奋争,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看与“权力市场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的她,能活出多少生命能量来。
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赠予刘虹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她觉得至今还很难说已梳理清楚。但有一条可谓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像她所自我调侃的,她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她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她对精神生活有着非常强烈渴望,如果有半口饭吃,就会想着精神上的追求。她苦苦思索: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她发现,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你是谁?你到底要什麽?你如何要?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而刘虹坚定地紧握着这把钥匙,拒绝名利物欲诱惑,拒绝把浅近的目标当作归宿,拒绝把手段当成目的。
刘虹回顾,她一生基本都是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十五岁就参加“革命”,招为边境线上的小报务兵,太小就尝到了生活的阴暗面;长期的孤独感,加上一生体弱多病。总是在疾病中煎熬的她,有时真是把写作当成与生命赛跑,活一天,写一天。如写不动了,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看重生命的尊严和质量,不能想象重病缠身、苟延残喘、乞人怜悯、不能思考和写作的日子是不是需要过下去……总之,多病甚至也成为她目前写作的动力,怀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要只争朝夕。她又有太多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骨子里极悲观,而她本来的天性是开朗活泼的。这样,刘虹一直有一种悲哀:健硕的灵魂追求,与病弱的肉体之间,构成她生命的矛盾冲突。对此她曾报以苦笑——也好,否则她可能早就成了行动上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了。
在孤独、痛苦和高压下,刘虹却始终能持守率真、正直的天性,绝不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卑躬屈膝、拍马钻营、苟且媚俗。正如刘虹自己所说: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裡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为此,她把一代大师陈寅恪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五
刘虹曾在诗集《结局与开始》后记中,把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盘点:前一阶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後一阶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大地忧思”正如当时的朦胧诗那样,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意识,包括对民族劣根性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对“文革”和中国苦难的反思。
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摸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刘虹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地忧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她那时是跳出来客观地观察比较多,有些“隔”;而她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如论者所说,如果把她的《致乳房》与同时创作的《打工的名字》放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她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她的后期创作主题“存在之痛”向前期主题“大地忧思”的重生性叠合与深化。一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是有着更多自寻的痛苦,所以刘虹为什么会写到“临界状态”、“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锐利的感觉。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族的痛苦——从痛感出发,她觉得就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而以前多是从“思考”出发。而现在走到了“痛感写作”,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她说她的诗写经验若缩为一句话,就是鲁迅那句名言: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好诗必须和诗人的灵魂一起熔炼;诗是活出来的,不仅仅靠舞文弄墨。
刘虹声称她特别为俄罗斯民族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她说,如果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风格,那么守住悲壮和沉郁也是一种大美,一种有力度的美。她诘问:“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但在苦难中坚守高贵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必然要在思想上、乃至生存上均要承受残酷的而且无穷的煎熬。
今天中国大陆,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座标上,太多的人赶着歌颂“盛世”太平、炮制“主旋律”还来不及,或者与时俱进,投合商业需要,及时以文字换取物质利益;而刘虹却恪守“精神边缘主义”,追求前瞻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向往坚持自由思想、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永不合作的姿态,希冀自己永远能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冥冥之中,生命的走向似乎遵循一条坚韧的、内在的轨迹:刘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多岁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她身上可能永难一致。然而,她更看重的是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她的真情实感。那么,既然刘虹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怎么会特别惠及于她呢?
可能在深层的、也许是永恒的意义上,对刘虹更为残酷更难解脱的折磨还不是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刘虹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她说: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然后才能做女人。不能过分标榜女性诗歌、女性写作,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
基于这种观点,在2003年9月“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珠海诗歌论坛上,当广州一位女诗人强调女性生理、心理、情感上的特点,强调女性诗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都有别于男性,并呼吁男士们更多地关注、评论女性诗歌时,刘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下文坛的真问题或曰更紧迫的问题是: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人”,而不要因袭乃至迎合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女性定位——热衷于成为男权社会的“被看”。刘虹这几年还反复强调: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诗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刘虹对那种给诗涂口红、穿露脐装,甚至涂上经血的所谓“女性意识”更是不屑与为谋。这样,刘虹是占据了一个诗写理论的高地,但这个高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大潮的包围、冲击下,周边已出现许多流失;而站在这个高地上的刘虹不免显得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刘虹的“精神的洁癖”的极致是她对爱情的真谛的坚守;作为反面,是对情场变商场、真爱缺席的愤激和悲哀。这是她多年诗写的一个核心主题。早在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的早期代表作《向大海》一诗中,刘虹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抒发她对理想对象的追寻、张扬她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了。值得注意的是,她当时就已经有了预感,这种理想境界决不容易达到,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而假如这种理想境界无法达到的话,“将是我一生的——惨败!……”。在诗中,甚至出现这些不祥的哀叹:“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显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灾难,藏在刘虹灵魂深处;而人性中永远无法完全彻底摆脱的动物性,便是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我看了刘虹写于2004年3月题为《找对象》的关于爱情哲理的随笔后,我就对她说:“犹如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在文学艺术中才能实现,完全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你起码早生了三百年。”
如论者所言,“刘虹像赴深渊一样献身于爱情,献身于诗,又写出深渊一样的女人,深渊一样的诗,使她的诗成为爱情的绝唱,也成为女人的绝唱。”类似下面的雄论也是正确的:越是理想主义者,越是在灵魂深处潜藏着悲哀,也正是在悲哀的生存境况中,才使得理想主义更加光彩夺目。但听听刘虹自己的诉说吧:
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绝望。或者说,是害怕面对绝望。我曾随手记下一个词:绝境书写——书写绝境。而这倒反而比十年前平心静气和得多,从容得多,因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么在等着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
其实,我的诗全是蘸着自己的生命之痛写的。是的,痛苦是我诗歌的源泉……
六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当我读到《致乳房》一诗的这个结句,我震悚了。
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命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预言!
或者这就是刘虹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刘虹的命运似乎带有悲剧性,这是她秉持的理想主义在当下语境所难以逃脱的宿命。她将来终有一天到了谢幕的时候,只是,谢幕之后,必定在中国诗写历史上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此文曾发表于2005年第3期《中外诗歌研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期刊);收入《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2006年12月台湾出版);提交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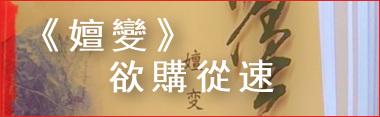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