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
(在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大会上的讲话稿)
各位老师好!由于时间所限,我从长篇演讲稿《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后半部分缩写成这篇发言,故难免在逻辑上、举例上等等方面都会有所疏漏,权作抛砖引玉吧。
先谈写作的大前提,这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整体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
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一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再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我于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我的女性言说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特区的她们》等,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病态扭曲。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比如《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等。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比如《有一种女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男人女人》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扭曲的女性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第五,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其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
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访谈问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回答说: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男女两性的平等“对视”,“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
记者还问到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认为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言说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绽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展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成长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谢谢大家!
2. 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在悉尼的演讲)
今天能来到这里分享写作心得,与大家交流切磋、共同成长,非常高兴!
首先要感谢山林、千波、张劲帆等老师的辛苦筹划、精心安排,还要感谢拨冗光临现场的本地作家诗人们!
我的演讲题目是:《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身为一个女性诗人,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女性写作的主体性问题——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面对书写客体,怎样以现代文明意识来观照和表达女性群体的当下境况、历史命运和精神成长;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书写主体,女性作家怎样不断自我完善其独立人格、思想追求和公民素质,以期在作品中彰显现代女性应有的丰富性,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女性整体的存在真相和发展方向,为女性群体乃至整个族群发声。
下面分为3个方面来谈今天的话题:
一、简介我的女性题材写作的经历和社会反响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上海《文学报》对我专访时,就给我出了这个大题目:谈谈你的女性写作立场。
可能因为自己属于精神追求比较强烈的人,至今被朋友们称作“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尤其经历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当时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精神飞扬的年代,我生吞活剥读了不少新引进的现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的书籍。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始关注这块土地上女性群体的现实遭际和历史命运。198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题材的诗作,比如1985年发在《人民文学》的《读雷诺阿<少女像>》,之后还有《诗刊》《华夏诗报》《青年文学》等报刊。近20年来,我更是越来越多地涉及该主题,发表了大量作品。比如在《光明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世界》、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紫丁香诗刊》,澳门《中西诗歌》,《香港散文诗》,美国《新大陆》、《亚省时报》《常春藤》诗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此外《中华文学选刊》发在扉页的《致乳房》;《花城》上的《女书》组诗12首等。还有咱们《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多年前就由何与怀博士热心引荐陆续发表了我数十篇作品、包括女性题材作品 。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的解放程度。”所言极是!这不仅是考察客观社会的标杆,更是女作家自查自省、乃至自我存在的使命。
我持续多年的女性话题书写,在海内外文坛引发了不少关注和好评。比如台湾著名诗人向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论《丰富而不凡的女性言说》;《文艺报》蒋登科的评论《刘虹:拒绝与坚守》;《诗刊》海上的评论《自由心性与良知》;《文学自由谈》向卫国的评论《追求诗歌的“重”与“大”》;《阅读与写作》赵思运的评论《刘虹诗歌的女性言说》;《澳洲新报》上的何与怀博士的刘虹访谈《对话:精神贵族与现代女性诗写》;台湾《艺文论坛》的刘虹访谈《女性诗歌:根部意识与现代精神》;香港《夏声拾韵》上的《诗歌是我俗世的飞翔——刘虹访谈录》;评论家唐晓渡发在《绿风》和《特区文学》上的《评刘虹的诗<沙发>》;以及国内外著名评论家和诗人孙绍振、鲁原、陈超、张清华、耿占春、李建军、何与怀、王岳川、李小雨、韩作荣、王燕生、向卫国、张德明、、周思明等对我第6部诗集中女性话题作品的评论等等。此外,在第13届国际诗人笔会上,我宣读了论文《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
这里节录一段同为女性诗人的原《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的评论:
“刘虹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优秀的女诗人,首先要突破的是性别,也就是说首先是诗人,而不是女诗人。大气、纯粹,这正是刘虹的诗最令人欣赏的地方。思想的光芒使女诗人显出不同寻常的可爱。”
另一位著名诗评家赵思运也谈到我作品性别表达的特征:
“刘虹的诗充满了丰富的诗学辩证法:一方面,把性别意识发挥到极致,考量女性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又在价值立场上极力淡化了性别意识,而凸显出普适的“人”的立场。一方面张扬俄罗斯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语境。一方面,打开女性的丰富而充盈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又涤荡了风花雪月的脂粉气,而通向骨气奇高的理性之境。将对立的两极力量平衡起来的诗艺,对于诗人是很大考验,而刘虹无疑是化险为夷的。”
“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曾是我多年前研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奠基人西蒙·波伏娃著名的《第二性》一书的心得概括,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目标,以及写作时的精神向度。然而,我越来越发现,现实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在一个传统劣根顽强因袭加现代文明精神缺位的土地上,一个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考、性灵绽放、看重精神价值的女性,越努力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越与现实中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人”标准背道而驰,以致遭遇更多的人生磨难……毋庸讳言,在世俗世界里,这几成今天的一道“中国特色”风景……
其实,在有些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地方,男人也同样:想不谄肩胁背、挺直腰杆不妥协、不流俗地做人,那多半会被俗世所不容。
——正因为此,我才要用自己诗笔真诚地呼吁:
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要先成为人——题中之义包括:去努力拓展人之成为人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理想追求,才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丰富完整的女人(或男人);这辈子可以不做世俗世界的所谓“成功女人”,却应该努力地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大写的——人!同时,作家只有不断历练成长为人,才有可能写出具有灵魂质量、思想份量和历史重量的好作品。
二、是何、为何、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我认同的“女性写作立场”主要包括:
首先,树立健康的写作理念。多年前在《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写作理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写作的大前提,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据此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为何要倾注于女性言说?简而言之,若把我用诗歌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归结为几个字,可曰:痛切感!这正是我写作女性题材的强大内驱力和持久的激情之源。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作家诗人,就总是怀有“忧天下之忧”的悲悯情怀,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疼痛感,方可对社会不断发出追问,不断标出新的审美高度以促社会进步。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大家知道: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应有现实针对性。而我在诗写中强调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进而才可以做好女诗人,正是在感官欲望疯狂膨胀、市场化语境格外形而下的今天,对严重误导女性成长的病态环境的坚决抵抗与观念反拨。我的展现大体可归结为5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发在《星星》诗刊上的《特区的她们》,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扭曲(此诗曾获全国大赛一等奖)。发在《花城》的《让我提前进入老妇的生活》、《男人需要的女人》、《趟不过男人河的女人》等,揭示女性当代生存的悖论。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题世界名画》、《我歌颂重和大》也涉及此类的话题。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我曾在报社新闻热线值班,接到过多个打工妹呼救的电话。为何说打工妹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她们往往多承受了一重性别的不安全感、甚至来自打工仔的情场欺侮。我直接面对这个群体创作了《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读新闻打工少女跳楼宁死不卖淫有感》。后一首诗沉痛到冷峻荒诞感的地步:我书写的立足点并非常规角度的同情跳楼者、谴责施害者,而是着重表达对蒙昧看客和无视生命的传统贞洁观的愤怒,对促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和陈腐文化的尖锐批判。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发表的此类作品主要有《有一种女人》《女诗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让我扮一回淑女》《男人女人》《情书里的她们》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女性的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下面我 朗读《沙发》: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
夕照里,更妩媚了它
穿着真皮的微笑
它谦恭迎纳的姿态
使事物坚硬的一端
顿时服软
它曾是客座
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
天伦之乐的部分
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
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
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
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
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
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
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
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
女性胸怀
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
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
谁将与惰性调情
陪春心落寞,谁将
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
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
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
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
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
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
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
丧失呐喊
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
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
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
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
模棱两可,中庸,苟且
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
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
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
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
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
皮笑肉不笑上
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
要隆起更多的柔软
去碰硬
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
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
跪成一排!
此刻,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
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
都像是……正中下怀
它甚至怯怯地问——
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第五,除了上述四个角度的表达,我还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以期得以疗治推动社会进步。其中的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那天恰逢三八妇女节)。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
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 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下面我节选朗诵:全诗共五节,每节11行,为省时间我只读头尾两节。
《致乳房》
——写在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一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
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
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
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
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
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
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五
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
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
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
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
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
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
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我的女性书写,在从以上五个方面展现我的指认、揭批和吁求之外,我还试图挑破一个可谓集体无意识的误区——我深深感到,我国多年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扭曲之至,只强调经济地位提升和独立之类外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格平等、精神独立这一更内在的现代素质,这导致了大量女性除了把自己“解放”得跟男人比“粗”比“悍”之外(这当然与男女干一样活儿强顶半边天、不顾性别差异地“被解放”有极大关系,仅这一点社会就难辞其咎),而自我立身之本的尊严意识、精神独立却极为欠缺。对此,在我的女性题材写作中给予了劝诫式的关注。比如在《深圳打工妹》组诗中的《白领小芳的幸福生活》、《小妹》,以及《特区的她们》一诗中对那些或被迫、或自觉地“活在男人眼睛里”中、充满交易意识的女性,就表达了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我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 ,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
说到这儿,我想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厌女症深刻且犀利的剖析。她指出,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对女性的蔑视,在女性身上则体现为自我厌恶,这一洞察深入到性别文化的骨髓,让人们看到性别不平等如何在潜意识层面运作。她还针对女性群体强调:“保持个体的独特性、自由,比追求平等的对待更加重要。”
多年来,我的女性写作立场首先是从我自己的观察、自省、读书等等经历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这期间自然也接受了从西蒙-波伏娃、伍尔芙、杜拉斯到上野千鹤子等杰出女性主义作家的重要启发,使我关于女性写作的立场也愈发明确一一比如在写作中,我不仅仅会关注仍处于父权社会的女性生存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声音,而是更加强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我解放,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想,生命价值的绽放。这首先就要克服内心的自厌、自卑、自弱、自我放弃,突破内在的枷锁。
我15年前出版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书中用了整整一辑来多维度地表达我的女性写作立场,这一专辑命名为“女书”。其中一些诗作如《有一种女人》《致女儿》《螺帽与螺钉》《特区的她们》《沙发》《致乳房》等等,曾广获好评,被多次转载、选刋。近年我的女性书写则更多为独白式,如《自首书》《我的性别简历》《梦》《漂亮女人存在之学》《挺好》《我和我的母系基因》等等。
回到上面朗读过的《沙发》,这是21年前看着我家的沙发写的,力求深入针贬在社会客观压力和女性自身退缩这两者同谋下,所导致的女性身心的奴役状态如何达到司空见惯且不自觉的程度。现在看来,这首诗的主题也恰恰对应了上野千鹤子的那句名言:“因为无法逃离而强行养成的忍耐力,是奴隶的宽容。”
毫无疑问,身为女性作家,我们在成为“人”的过程中,首先应同整个女性群体一样:摒弃这种古朽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奴隶的宽容”,并用笔充分地表达我们挺直的脊梁。
曾有记者问我,“写作时你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我的回答是:不!不是这样。性别在我的诗写中,除了起到题材视野有所侧重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健康写作理念的作家,首先是要站在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现代人的立场。如过分夸大性别在写作中的作用,总让人疑惑这可能多半是一种“营销”策略吧?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上这种“策略”还少么?比如那时泛滥文坛眼花缭乱的旗号和炒作:“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小女人散文”等等。
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起点,“身体写作”对于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统治,无疑曾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似乎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我们就念歪了经,过于痴迷于形而下的身体抚摸、欲望展销,却忽视了“身体写作”中更重要的对女性完整的生命体验的发掘(包含肉的,更包括灵的)。所以,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作家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性别的区分。如不先界定和展示你在动物界的种属,岂不容易堕入论公母而非论男女的荒诞中?显然,先成为人,继而作为人而为文,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可跨越的前提。
面对种种社会病相,我愿把女性题材书写,当作是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当作新时代妇女自我解放、精神现代化的新启蒙。
(这里插一段“轶事”:著名女作家张洁谈到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介绍时曾激愤地说:“我干吗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我很欣赏张洁这种拒绝搔首弄姿卖弄性别的“大女人气”)。
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还问到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认为,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一种女人与男人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
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曾有论者将《向大海》与舒婷的爱情诗名篇《致橡树》相提并论,而我可能更多地聚焦于相互独立、各自丰盈强大的男女两性,怎样在“对视”即平等对话中,达到深层的互相呼应、互相容纳,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自洽与包容。而当它指向个体时,无疑将成就爱情的最高境界。
是的,从“人”的立场出发,张扬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强精神和自由心灵的现代意识,这是我诗写中主要的“女性视角”,并力求开阔以达高远。
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下面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至于“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而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关注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探寻普遍的人性意义;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宽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主要特征: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
在我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研讨会上,记者采访我说:你的诗十分关注现实,比如闻名遐迩的《打工的名字》等关注底层劳动者;《我歌颂重和大》《说白》等扫描透视社会病状。在诗歌和诗人越来越倾向于内心,倾向于自我的年代,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你诗风的独特之处?
我回答说:向内或向外,只是诗写路数的不同,这与写不写得出好诗无关。向内的倾述,关键是看诗中的“自我”是否有足够的分量、能否“倾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况味与价值追寻?但无论怎样,自我倾诉不能过滥,一味自我抚摸以致成为自恋的表演。诗人还是要更多地睁眼看世界,成为怀抱悲悯之心替这个世界喊疼的人。这至少是一个健康人格的存在姿态所要求的,更是文学的道义担当和写作的意义所要求的。
(这里插几句:我近年的写作,较之过去更加深切地关注社会现实,诗也越写越干巴锋利,曾自嘲:我写的是“杂文诗”,至少在咱们《澳洲新报》发表的数十首诗中多半可归于此类(多用的笔名)——我实在是不吐不快啊!我视精准犀利的表达为第一,管他什么文体,若为此丢了诗人的名号,那就丢吧,呵呵……事实上,22前我的长诗《打工的名字》被海内外广泛转载时,其中就包括《中国杂文选刊》,分两次转载的).
其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对诗人的特别要求,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 “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笔。我曾这样强调过自己的写作理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有评论家把我的写作特征归类为“抽象现实主义”,以及区别于一般女诗人的“厚重与大气”。我想,这是在肯定我对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的追求吧。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我着意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这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飘落的树叶》《深圳打工妹》等,以及近年的大量诗作,比如《敏感词》《说小》《指望》《今日说法》《形式逻辑里的人民》等等,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我希望不断地丰富、升华、包括矫正自己的认知,坚定地从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立场出发,不断增强对现实社会洞悉、命名和批判的能力,使我的诗笔更加具有穿透力。
为便于大家理解“抽象现实主义”,我节选《打工的名字》朗读一小节:
C.
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
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
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
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
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
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
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
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
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
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
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
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
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从上大约可见,诗思力求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做名与实之间或名与名之间反复穿越。这是谈到我嘱意的诗写风格之一,略举一例,今天不能展开说。
谈到我追求的好诗?记得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我所追求的好诗,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诗歌;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的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
具体在风格上我的爱好比较宽泛,不拘于某一类型。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要诗人和之后的“不合作者”诗人,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其他还有现代欧美重要诗人里尔克、艾略特、普拉斯、叶芝、米沃什、奥登、希尼、帕斯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每读她的诗,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环境、长久的暴政打击,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常常为她、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文学艺术的追求过程,就是求真、向善和寻美的过程。在作品的思想力度上,我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或曰“求真价值”)摆在首位,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坛多年来的一个乱象——有些诗人不经过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以求获得理性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只凭一己一时的小感觉写作,常以思维的浅薄和混乱冒充“朦胧美”,或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内容的苍白。须知,真正的大诗人,都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格局。 关于这一点,著名评论家陈超在诗论集《打开诗歌的漂流瓶》中曾有明确的表达:“文学写作在强调‘心灵’之外,也要看重‘头脑’。”我的理解是,前者更多的表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对世界判断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发现与深刻)——此乃“大气”的前提。毫无疑问,真与善,是美的基础,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那么,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评论家敬文东曾倡导“诗歌伦理学”,他把“无发现”视作“不道德的诗作”。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现象世界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作家的重要写作目标。
而思想深度,无疑来自于作家顽强的求真意志。这不仅要善于概括提炼直接经验(自身体悟)与间接经验(他人总结),而且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偏重审美表达中的“感觉”、“意会”;夸大形象思维而贬抑抽象思维;处世做人上则要求“藏锋守拙”、“难得糊涂”,以及不求真理但求人情的“面子主义”。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顺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这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和高压治理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我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轻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的意思,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著的关注和批判。”我深以为然。一个从“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权去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包括权贵市场经济、官场腐败、权力通吃和阻挠政体改革等等),这正是当下作家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
我始终认为:诗人应该保持精神的洁癖。我很欣赏作家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对于女性,尤其女诗人,这种自爱,更是尊严的象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说得好:“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的确,诗歌写作,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以决绝的姿态与世界相拥的方式;它顽强地证明着我的生命存在,且不断校正着我的感性与理性、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失衡,使我葆有心灵的持续健康和丰富。同时,在客观上,我的诗写能对世上的真善美有所促进,至少有所吁求,这令我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之于我,不啻为一种俗世的拯救;或者说,是在肉身沉重的俗世间心灵的飞翔。
最后,朗读我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向大海》中的一小节,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篇:
《向大海》
——写于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
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
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
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
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
倾听你深沉的叹息
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
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
也许我指尖走漏过
一叶白帆的潇洒
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
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
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
这使我顿感卑微
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
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
渲染葬礼
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
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
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
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
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
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
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
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
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
有谁知道,你的浩瀚
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
一行诗的剪影
一句箴言
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
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
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
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
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
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
……
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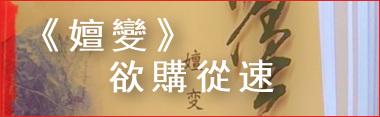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