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
2018年7月18日完稿于悉尼
第一节: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p323-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第二节: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內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 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 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 /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三节:“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2018年10月,西贝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开会时所摄。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作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第四节: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Rodney Milgate)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Robyn Ianssen(楊舜)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澳华画家范东旺作品《树》(丙烯画,90×90 cm)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向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第五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努力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水墨画《奇景》(《Miracle》)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神?/乳汁里混合着爱与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凈化。凈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2006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 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水墨画《双视图》(《Double View》)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第六节: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这是诗的最后一节:
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脆弱的/完美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籍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第七节: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何与怀博士在西贝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论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第八节:《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 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何与怀博士与吕进教授、梁上泉先生(左),蒋登科教授(右)摄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第九节: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 ,Owl Publishing, 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在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來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來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2018年9月,西贝在美国密苏里河边。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节: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2016年9月12日,南溟出版基金为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西贝前坐右四)。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面具》插图(澳华画家吴棣作品)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注: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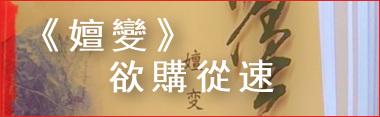

发表回复